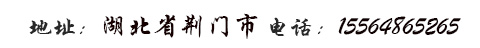梅雨时节,芭蕉叶大栀子肥
|
群芳谱上,百花争艳。所争者,无非形、色、香,得一即为名品,或有兼二者,却罕有三美并称的。栀子花形如拳而玲珑,花色如玉而皎洁,花香如冽而馥郁,正是难能稀有地集三美于一身的珍葩之一。但它在众香国中的席位,却远不及梅花、牡丹、芍药、海棠、兰花、荷花、桂花、菊花、芙蓉、水仙等。原因何在呢?我想,当与它开放后的衰萎也速而且狼藉也甚有相当的关系。 当梅雨方生,一片江南霏暗之中,油绿浓翠的栀子叶丛中,一夜之间绽放出朵朵琼瑶般的花头,上面还带着露珠,晶莹剔透,香气袭人,令人神清气爽,烦闷涤尽。然而,不过两天的时间,清纯的靓丽,忽然便成了一坨坨污秽的形色,佛头着粪般颓废委顿地散落在葱碧的枝头叶间,夹杂在新放的荳蔻年华中,久久不落。相比于其他花卉凋谢时的香销玉殒之美,不免大煞风景。 栀子有好几个别名,其中最典雅的一个叫“薝蔔”,系梵文的音译;亦作旃簛迦、赡博迦,一看便是外来语,远没有薝蔔来得“信、达、雅”。据《一切经音义》,佛教以十万香花作供养,尤以五树六花中的薝蔔香色殊胜,无比稀有,不可思议。所以,佛教传入中国之后,东晋人便把原产我国的栀子认作是西域的薝蔔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“广动植木”有云:“陶贞白言,栀子翦花六出,刻房七道,其花香甚。相传即西域薝蔔花也。”至明方以智《通雅》,始以为非是。今天的植物学家进一步考证出薝蔔实为木兰科的黄兰,与茜草科的栀子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。 宋佚名《百花图卷》之栀子八哥 但我作诗作画,于栀子仍喜欢以“薝蔔”名之而知错不改。这不仅是为了承续前贤千百年来的诗画传统,更因为栀子的从绽放到凋谢,使我联想起《释迦谱》中所讲到的一则故事:释迦修道将成,魔王波旬惧其成道后的法力,便派鬼卒明火执仗向其发动进攻,释迦不为所动,武力尽化灰烬;又遣三个美貌的女儿前往引诱,欲以姿容颜色“乱其净行”: 女诣菩萨(释迦),绮语作姿,三十有二姿,上下唇口,嫈嫇细视,现其陛脚,露其手臂,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。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术,而自言曰:“我等年在盛时,天女端正,莫逾我者,愿得晨起夜寐,供事左右。”菩萨答曰:“汝有宿福,受得天身,形体虽好,而行为不端,革囊盛臭。尔来何为?去!吾不用。”其魔女化成老母,不能自复。 这一故事,在克孜尔石窟、库木吐拉石窟、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的壁画、浮雕中多有表现,名为《降魔变》。以莫高窟窟的北周壁画(下图)为例,释迦结跏趺坐于画面中央,结降魔印,安忍不动,默如雷霆;上方为群魔乱舞,张弓、搭箭、持枪、抡斧、执蛇,气势汹汹地向佛扑去;下方左侧为三魔女青春靓丽向佛献媚,右侧已变成三个丑婆,“头白面皱,齿落垂涎,肉削骨立,腹大如鼓”,自惭形秽。这刹那之间的美丑衰变,与栀子花的由极清纯而极污秽,不正相吻合吗?则即使栀子不是薝蔔花,也应是天魔女,与佛教的说教是脱不了干系的。 有了这一认识,重新再来审美栀子的香馥。恍然回味到它有别于其他花卉、包括同样浓烈的桂花的香而清,而有一种类似于巴黎香水般香而腻的异域风情。我曾于星洲观赏洋兰,惊艳之余,以为国兰之美如窈窕淑女而妩媚动人,洋兰之美则如浪荡胡姬而狐媚迷人。栀子的形色,清真雅正,所体认的是典型的中华审美,但它的香馥,浓烈郁腻,总使人觉得像是异域的浪漫风情。 “花气熏人欲破禅”。栀子还有一个别名叫“禅友”,它的含义,应该正是“破禅最是栀子花”吧?栀子的玲珑之形、冰玉之色、馥郁之香,兼清纯与狐媚,“我见犹怜”;则即使它明日便狼藉地凋零委顿,“传语风光共流转,暂时相赏莫相违”(杜甫《曲江》),又何妨我今天及时的赏心悦目呢? 佛教的一切“受想行识”,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,乃至“空中无色,无受想行识”。所以,释迦视魔女的美色为老妪的污秽而“去”之“不用”。但我辈凡夫俗子,执色为空,不如见色受色、见空受空,于栀子专赏其今日之清纯靓丽,无论其明日之芜秽萎绝。就像越是彻悟到“欢乐极兮哀情多,少壮几时兮奈老何”(汉武帝《秋风辞》),就越应该加倍地珍惜眼前的“欢乐”、“少壮”一样。 (元)钱选:栀子图 自古以来的诗人、画家,于栀子的歌咏、描绘,无不着眼于它的明丽而无视其芜秽,盖可以概见之矣。 我于栀子的受想行识,始于少年时代。当时的农村,基本上没有种植观赏花卉的,但远村有一座老宅,天井的墙角有一株几十年的栀子,高达2米,茂密得很。每到梅雨季节,便绽放出冰花朵朵,给闷湿的空气带来清新凉爽。今天,每一个花园社区的绿化多有以栀子为主要植花的,而且有高株、矮株、重瓣、单瓣的多个品种,成为海棠、紫藤等春花以后主要的赏花景观。接下来,便是赏荷了;之后,赏桂、赏菊、赏梅、赏山茶,一年四季,花事无有间断。任一小区的空间,简直“空即是色”。 观花寻诗,读诗识花,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。所以,我很早就知道了栀子的别名叫薝蔔,尤对宋朱淑真的“一根曾寄小峰峦,薝蔔香清水影寒;玉质自然无暑意,更宜移向月中看”印象深刻,诚所谓“色空空色,明月前身”。同时也学着自己做,不过率汰胡诌,打油自喜,覆酱嫌粗。70年代后知道了一点格律的知识,慢慢地开始进入诗词的门户,但随写随弃,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的。因为,当时的写诗只是为了一时的兴趣,包括咏栀子在内,犹如“相逢开口笑,过后不思量”。所以乘兴而写,兴尽而弃,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来会同诗画打交道并被人误认为小有成就。就像樱花并不是为了凋谢时的美丽而绽放,栀子更不会因为凋谢时的委顿而不绽放。 (明)沈周:栀子图 每有研究齐白石的专家讲到,白石老人的阔笔花卉配以工细草虫,是因为预见到晚年后会享大名,而届时画不出工细的形象了,所以趁年轻时画了许多虫子却不配景,留待晚年后补成。但大多数人,事实上是很难预测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和成就的,所以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为几十年后的“大成”保存今天的“少作”资料。不仅卑微如我,当年在农村种地时根本没有妄想过有一天会跳出“龙门”,涉事高雅的文艺。就是谢稚柳先生,从小生活在诗人圈里,他早年所写的诗词,也多没有保存下来。 众所周知,谢老的诗词是从李义山、李长吉起手入门的。但今天所见,纯粹是宋人的平实风格,于二李的谲丽几乎毫无瓜葛。原来,我们所见之诗都是抗战避兵重庆之后,尤其是维新以来的作品,谢老因沈尹默先生的规劝而转向了宋人。然而,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见到部分散佚民间的谢老《词稿》,以陈老莲体的小行楷誊录于“调啸阁”诗笺上,多为40年代之前的作品。一种呕心沥血、迷离瑰丽的穷工极妍,与后来的“不耐细究”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但当年的谢老并没有“敝帚自珍”,以致后来陆续整理《鱼饮诗稿》《甲丁诗词》《壮暮堂诗词》《壮暮堂诗钞》时,都没能收集到这部分真正体现其学二李风格的佳作。 徐建融:蝶影蔔香 我之留意保存自己的诗稿,应该是在年为谢老搜集、编辑《壮暮堂诗钞》之后。凭记忆回想了之前的所作,只能到七八十年代;此后的吟诵也尽可能留下了底稿。这阕《满庭芳·自题栀子写生小卷》,应该便是在这前后所填: 一片江南,绵绵昼夜,梅雨看洗青黄。更谁知有,薝蔔出银潢。暑色霪霪搓白,三六出、弄玉斯降。凝香雪,鼻端消息,渐冽愈迷茫。 琳琅。初霁后,天凉如水,月影东墙。照空色无形,馥起浪浪。且向旃檀海里,快参透、抛却皮囊。花微笑,何须煮酒,自在渡慈航。 词中的“三六出”,缘于古诗词中的“六出灵葩”。刚读到时,颇有疑惑。因为,“六出”的花朵,通常为球根类的草本,如水仙、萱草、百合等;栀子为常绿灌木,花瓣甚夥,虽未曾细数,但当不止六出。后来一数,为十八瓣,乃暗讥古人格物的粗疏。转念一想,或许不是为花写实,而是因其花色如雪,以雪花六出故拟之。又后来,见到矮株单瓣的栀子,果然是六出!再检重瓣者,原来十八瓣分为三层,逐层绽放,每层为六出!乃知古人审物不苟,反是我走马观花、浅尝辄止了。 古人咏栀子的诗词甚多且美,但画栀子的图绘相对而言却并不多见。我最早见到的以栀子为画材,是谢老写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的诗意(上图),觉得花头之美如荷花,于是也开始画栀子。但当时的栀子种植并不普遍,连远村老宅中的那一株也被砍了,所以对花写生是要多方寻访、骑自行车前往的。后来又见到宋人的、钱选的、陈淳的栀子,尽管图片印得很不清晰,还是认真地作对本临摹。新世纪后,搬入园林化的小区,年年梅雨,都浸淫在薝蔔香中;古画的印刷,更仅“下真迹一等”,画栀子才渐入佳境。双勾的,点厾的,设色的,水墨的,绢本的,纸本的,熟宣的,生宣的……不拘一格,体会日深而境界稍进,致使栀子,成了我最常画的花卉素材之一。庶使冰清玉洁的空色生香,破禅、悟禅,损亦友,益亦友,随缘而无执。 包括栀子在内,我的画上多题有诗文,倒不是因为志存风雅,而是因为性之所好,欲听还看两无厌,故将颜色染香音。而唐释皎然的《答李季兰》诗,尤得我于栀子的画胆诗心: 天女来相试,将花欲染衣; 禅心竟不起,还捧旧花归。 作者:徐建融 编辑:吴东昆 责任编辑:舒明 *文汇独家稿件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uihuaa.com/sgghs/1234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植物对生活的保健效果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